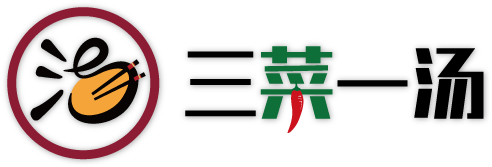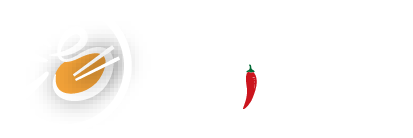小时候,爷爷家附近的大院子里满是黄花。那时并不知道那黄灿灿的花朵是可以拿来吃的,只是和几个要好的玩伴在花丛里钻来钻去,黄花的味道沾了满身,弄脏了儿时那条雪白雪白的裙。爷爷离休后便经常坐在家属院门前的那块厚重石头上远远的看着我撒着欢儿的玩,穿青灰色的汗衫,龙头拐杖被手掌磨得光滑,放在身边。在灌木丛中找红色的小果子时划伤了手,跑过去,把伤口晾在他眼前,不哭,他也不嗔怪,用旧布条儿把我划伤的手指包起来,带我回家。记忆中,和爷爷是极亲的,却很少言语。那个满是黄花味道的夏天突然变得那么远,远到真真儿的成了昨日。远到爷爷离开我已经那么那么多年。远到我在某天下午邂逅一大丛新鲜黄花时,突然被时光击垮,泪流满面。
你看,我们害怕的,果然不是新鲜黄花里的秋水仙碱。而是记忆,带着遥远的幽香,一遍又一遍的在心灵中,在胃里,在湿润的眼眶中,温暖,温暖,再温暖,直到疼痛。

微信小程序查看完整菜谱,还能赚积分哦~
肉爆双鲜收藏
浏览 178404
收藏 47
时间 30-45分钟 切墩(初级)
所需食材
- 新鲜黄花 300g
- 黑木耳
- 猪里脊肉
- 盐 适量
- 蒜 两瓣
- 油 适量
- 老抽 适量
- 香油 适量
肉爆双鲜的做法步骤
-
步骤 1:
新鲜黄花300g,摘出花瓣,在温盐水中浸泡20分钟左右,沥水备用。
-
步骤 2:
黑木耳泡发洗净切小朵,蒜两瓣切片,猪里脊肉切片。
-
步骤 3:
锅内放油,爆香蒜片后倒入肉片划炒至变色后滴入老抽大火翻炒,倒入木耳和黄花继续爆炒至软。
-
步骤 4:
调入盐和味精后熄火,烹入少许香油即可。
小贴士
鲜黄花里,含有秋水仙碱的是花蕊,所以只要去除花蕊只用花瓣来料理,就不用再担心中毒了,为了更为安全,把花梗也去除了,浪费了些,但吃得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