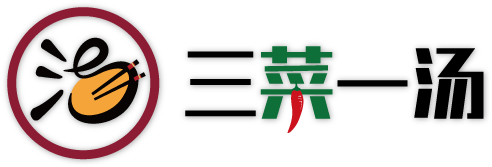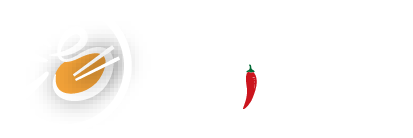天干物燥,风里是早春杨柳吐绿和尘土的味道,温暖扑鼻。厚重的棉衣洗净、叠好、放进床里的储物格子。色彩斑斓的裙衫都华丽丽的挂了起来,衣橱里一派生机盎然。
腰上赘肉犹在,生活中鸡零狗碎犹存,嘈杂市井的柴米油盐仍在继续,一如每个春夏秋冬的开始,给自己一卡车的梦想和计划,然后,大大咧咧的前行,偶尔停下来,看那些云卷云舒的风景。
变着法儿的吃西红柿,煎炒焖炸炖煮烧——去火降燥,连爽肤水都可以省略一半儿。
窝在地板上看书,书里男子问那个鼻梁上有雀斑的女孩儿,时间在你的耳朵里是什么声响?
女孩儿说,是哗啦一声,就像你翻书时的动静儿。
哪有那么缓慢的时光呢,缓慢得可以留个声响给记忆。那原本就是悄无声息的,安静得连回首的机会都不肯留给你。绝情得,连流连的闲暇都不给你。更何况,是那“哗啦”一声儿呢?

微信小程序查看完整菜谱,还能赚积分哦~
西红柿鸡蛋打卤面收藏
浏览 160162
收藏 99
时间 10-30分钟 切墩(初级)
所需食材
- 西红柿 4个
- 鸡蛋 3个
- 手擀面
- 葱花 15g
- 盐 5g
- 高汤 30g
- 热水 500ml左右
西红柿鸡蛋打卤面的做法步骤
-
步骤 1:
鸡蛋放入碗内打散,西红柿洗净切小块备用
-
步骤 2:
过热后倒入少许油,把打好的蛋液放入,用筷子划炒至碎后盛出
-
步骤 3:
锅洗净后重新倒入适量油,待油3成热时倒入葱花炒出香味后把西红柿块放入翻炒至起沙,调入盐翻炒均匀后注入沸水
-
步骤 4:
加入高汤或者高汤块(鸡精、鸡汁亦可),待食材沸腾后倒入炒好的蛋碎,搅拌均匀即可
-
步骤 5:
面条做法详见:http://www.douguo.com/cookbook/84261.html。 将西红柿打卤浇在面条上即可
小贴士
西红柿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胡萝卜素和B族维生素,与鸡蛋同食可以增强人体对蛋白质的吸收,同事还可以促进消化和骨骼生长,开胃降燥。